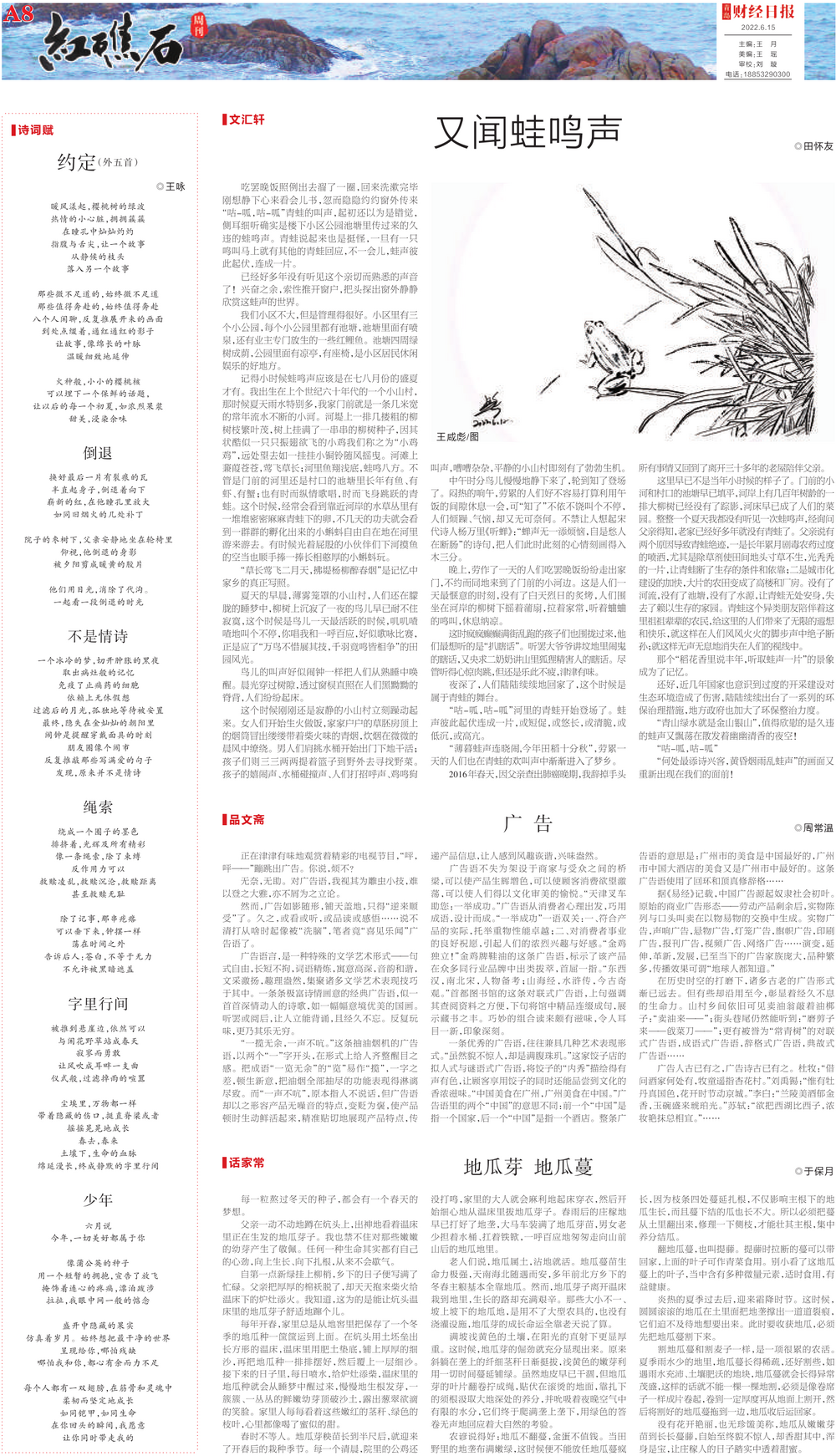吃罢晚饭照例出去溜了一圈,回来洗漱完毕刚想静下心来看会儿书,忽而隐隐约约窗外传来“咕-呱,咕-呱”青蛙的叫声,起初还以为是错觉,侧耳细听确实是楼下小区公园池塘里传过来的久违的蛙鸣声。青蛙说起来也是挺怪,一旦有一只鸣叫马上就有其他的青蛙回应,不一会儿,蛙声彼此起伏,连成一片。
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见这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了!兴奋之余,索性推开窗户,把头探出窗外静静欣赏这蛙声的世界。
我们小区不大,但是管理得很好。小区里有三个小公园,每个小公园里都有池塘,池塘里面有喷泉,还有业主专门放生的一些红鲤鱼。池塘四周绿树成荫,公园里面有凉亭,有座椅,是小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记得小时候蛙鸣声应该是在七八月份的盛夏才有。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小山村,那时候夏天雨水特别多,我家门前就是一条几米宽的常年流水不断的小河。河堤上一排几搂粗的柳树枝繁叶茂,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柳树种子,因其状酷似一只只振翅欲飞的小鸡我们称之为“小鸡鸡”,远处望去如一挂挂小铜铃随风摇曳。河滩上蒹葭苍苍,莺飞草长;河里鱼翔浅底,蛙鸣八方。不管是门前的河里还是村口的池塘里长年有鱼、有虾、有蟹;也有时而纵情歌唱,时而飞身跳跃的青蛙。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靠近河岸的水草丛里有一堆堆密密麻麻青蛙下的卵,不几天的功夫就会看到一群群的孵化出来的小蝌蚪自由自在地在河里游来游去。有时候光着屁股的小伙伴们下河摸鱼的空当也顺手捧一捧长相憨厚的小蝌蚪玩。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是记忆中家乡的真正写照。
夏天的早晨,薄雾笼罩的小山村,人们还在朦胧的睡梦中,柳树上沉寂了一夜的鸟儿早已耐不住寂寞,这个时候是鸟儿一天最活跃的时候,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你唱我和一呼百应,好似歌咏比赛,正是应了“万鸟不惜展其技,千羽竟鸣皆相争”的田园风光。
鸟儿的叫声好似闹钟一样把人们从熟睡中唤醒。晨光穿过树隙,透过窗棂直照在人们黑黝黝的脊背,人们纷纷起床。
这个时候刚刚还是寂静的小山村立刻躁动起来。女人们开始生火做饭,家家户户的草胚房顶上的烟筒冒出缕缕带着柴火味的青烟,炊烟在微微的晨风中缭绕。男人们肩挑水桶开始出门下地干活;孩子们则三三两两提着篮子到野外去寻找野菜。孩子的嬉闹声、水桶碰撞声、人们打招呼声、鸡鸣狗叫声,嘈嘈杂杂,平静的小山村即刻有了勃勃生机。
中午时分鸟儿慢慢地静下来了,轮到知了登场了。闷热的响午,劳累的人们好不容易打算利用午饭的间隙休息一会,可“知了”不依不饶叫个不停,人们烦躁、气恼,却又无可奈何。不禁让人想起宋代诗人杨万里《听蝉》:“蝉声无一添烦恼,自是愁人在断肠”的诗句,把人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晚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吃罢晚饭纷纷走出家门,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门前的小河边。这是人们一天最惬意的时刻,没有了白天烈日的炙烤,人们围坐在河岸的柳树下摇着蒲扇,拉着家常,听着蛐蛐的鸣叫,休息纳凉。
这时疯疯癫癫满街乱跑的孩子们也围拢过来,他们最想听的是“扒瞎话”。听罢大爷爷讲坟地里闹鬼的瞎话,又央求二奶奶讲山里狐狸精害人的瞎话。尽管听得心惊肉跳,但还是乐此不疲,津津有味。
夜深了,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家了,这个时候是属于青蛙的舞台。
“咕-呱,咕-呱”河里的青蛙开始登场了。蛙声彼此起伏连成一片,或短促,或悠长,或清脆,或低沉,或高亢。
“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劳累一天的人们也在青蛙的欢叫声中渐渐进入了梦乡。
2016年春天,因父亲查出肺癌晚期,我辞掉手头所有事情又回到了离开三十多年的老屋陪伴父亲。
这里早已不是当年小时候的样子了。门前的小河和村口的池塘早已填平,河岸上有几百年树龄的一排大柳树已经没有了踪影,河床早已成了人们的菜园。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有听见一次蛙鸣声,经询问父亲得知,老家已经好多年就没有青蛙了。父亲说有两个原因导致青蛙绝迹,一是长年累月剧毒农药过度的喷洒,尤其是除草剂使田间地头寸草不生,光秃秃的一片,让青蛙断了生存的条件和依靠;二是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大片的农田变成了高楼和厂房。没有了河流,没有了池塘,没有了水源,让青蛙无处安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青蛙这个异类朋友陪伴着这里祖祖辈辈的农民,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快乐,就这样在人们风风火火的脚步声中绝子断孙;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那个“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成为了记忆。
还好,近几年国家也意识到过度的开采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伤害,陆陆续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治理措施,地方政府也加大了环保整治力度。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值得欣慰的是久违的蛙声又飘荡在散发着幽幽清香的夜空!
“咕-呱,咕-呱”
“何处最添诗兴客,黄昏烟雨乱蛙声”的画面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