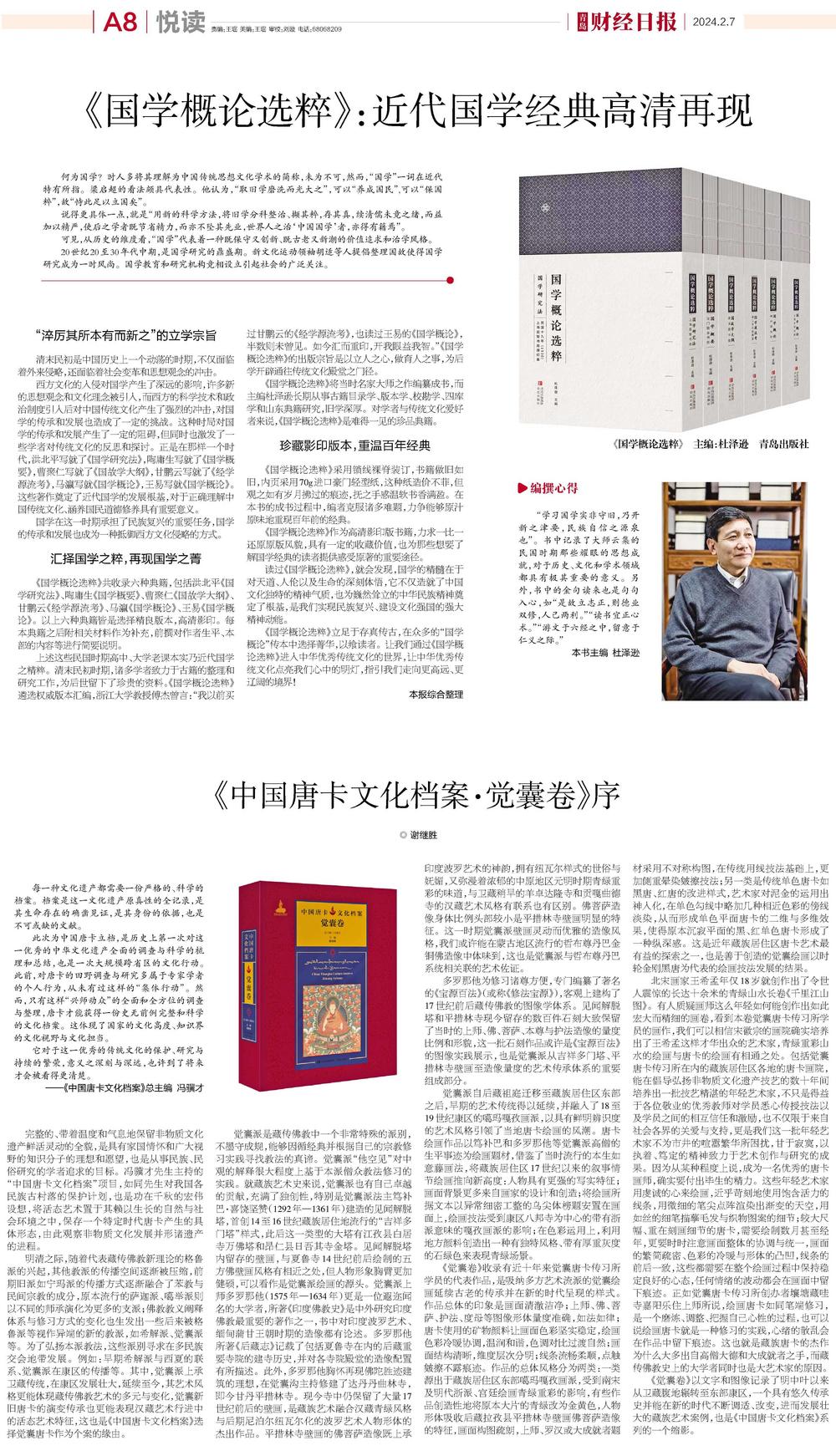◎ 谢继胜
每一种文化遗产都需要一份严格的、科学的档案。档案是这一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全记录,是其生命存在的确凿见证,是其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献。
此次为中国唐卡立档,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这一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全面的调查与科学的梳理和总结,也是一次大规模跨省区的文化行动。此前,对唐卡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多属于专家学者的个人行为,从未有过这样的“集体行动”。然而,只有这样“兴师动众”的全面和全方位的调查与整理,唐卡才能获得一份史无前例完整和科学的文化档案。这体现了国家的文化高度、知识界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担当。
它对于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研究与持续的繁荣,意义之深刻与深远,也许到了将来才会被看得更清楚。
——《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总主编 冯骥才
完整的、带着温度和气息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灵动的全貌,是具有家国情怀和广大视野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愿望,也是从事民族、民俗研究的学者追求的目标。冯骥才先生主持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如同先生对我国各民族古村落的保护计划,也是功在千秋的宏伟设想,将活态艺术置于其赖以生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保存一个特定时代唐卡产生的具体形态,由此观察非物质文化发展并形诸遗产的进程。
明清之际,随着代表藏传佛教新理论的格鲁派的兴起,其他教派的传播空间逐渐被压缩,前期旧派如宁玛派的传播方式逐渐融合了苯教与民间宗教的成分,原本流行的萨迦派、噶举派则以不同的师承演化为更多的支派;佛教教义阐释体系与修习方式的变化也生发出一些后来被格鲁派等视作异端的新的教派,如希解派、觉囊派等。为了弘扬本派教法,这些派别寻求在多民族交会地带发展。例如:早期希解派与西夏的联系、觉囊派在康区的传播等。其中,觉囊派上承卫藏传统,在康区发展壮大,延续至今,其艺术风格更能体现藏传佛教艺术的多元与变化,觉囊新旧唐卡的演变传承也更能表现汉藏艺术行进中的活态艺术特征,这也是《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选择觉囊唐卡作为个案的缘由。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派别,不墨守成规,能够因循经典并根据自己的宗教修习实践寻找教法的真谛。觉囊派“他空见”对中观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基于本派僧众教法修习的实践。就藏族艺术史来说,觉囊派也有自己卓越的贡献,充满了独创性,特别是觉囊派法主笃补巴·喜饶坚赞(1292年—1361年)建造的见闻解脱塔,首创14至16世纪藏族居住地流行的“吉祥多门塔”样式,此后这一类型的大塔有江孜县白居寺万佛塔和昂仁县日吾其寺金塔。见闻解脱塔内留存的壁画,与夏鲁寺14世纪前后绘制的五方佛壁画风格有相近之处,但人物形象胸臂更加健硕,可以看作是觉囊派绘画的源头。觉囊派上师多罗那他(1575年—1634年)更是一位遐迩闻名的大学者,所著《印度佛教史》是中外研究印度佛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对印度波罗艺术、缅甸蒲甘王朝时期的造像都有论述。多罗那他所著《后藏志》记载了包括夏鲁寺在内的后藏重要寺院的建寺历史,并对各寺院殿堂的造像配置有所描述。此外,多罗那他胸怀再现佛陀胜迹建筑的理想,在觉囊沟主持修建了达丹丹曲林寺,即今甘丹平措林寺。现今寺中仍保留了大量17世纪前后的壁画,是藏族艺术融合汉藏青绿风格与后期尼泊尔纽瓦尔化的波罗艺术人物形体的杰出作品。平措林寺壁画的佛菩萨造像既上承印度波罗艺术的神韵,拥有纽瓦尔样式的世俗与妩媚,又弥漫着浓郁的中原地区元明时期青绿重彩的味道,与卫藏稍早的羊卓达隆寺和贡嘎曲德寺的汉藏艺术风格有联系也有区别。佛菩萨造像身体比例头部较小是平措林寺壁画明显的特征。这一时期觉囊派壁画灵动而优雅的造像风格,我们或许能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哲布尊丹巴金铜佛造像中体味到,这也是觉囊派与哲布尊丹巴系统相关联的艺术佐证。
多罗那他为修习诸尊方便,专门编纂了著名的《宝源百法》(或称《修法宝源》),客观上建构了17世纪前后藏传佛教的图像学体系。见闻解脱塔和平措林寺现今留存的数百件石刻大致保留了当时的上师、佛、菩萨、本尊与护法造像的量度比例和形貌,这一批石刻作品或许是《宝源百法》的图像实践展示,也是觉囊派从吉祥多门塔、平措林寺壁画至造像量度的艺术传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觉囊派自后藏祖庭迁移至藏族居住区东部之后,早期的艺术传统得以延续,并融入了18至19世纪康区的噶玛嘎孜画派,以具有鲜明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引领了当地唐卡绘画的风潮。唐卡绘画作品以笃补巴和多罗那他等觉囊派高僧的生平事迹为绘画题材,借鉴了当时流行的本生如意藤画法,将藏族居住区17世纪以来的叙事情节绘画推向新高度:人物具有更强的写实特征;画面背景更多来自画家的设计和创造;将绘画所据文本以异常细密工整的乌尖体榜题安置在画面上,绘画技法受到康区八邦寺为中心的带有浙派意味的嘎孜画派的影响;在色彩运用上,利用地方颜料创造出一种有独特风格、带有厚重灰度的石绿色来表现青绿场景。
《觉囊卷》收录有近十年来觉囊唐卡传习所学员的代表作品,是吸纳多方艺术流派的觉囊绘画延续古老的传承并在新的时代呈现的样式。作品总体的印象是画面清澈洁净;上师、佛、菩萨、护法、度母等图像形体量度准确,如法如律;唐卡使用的矿物颜料让画面色彩坚实稳定,绘画色彩冷暖协调,温润和谐,色调对比过渡自然;画面结构清晰,维度层次分明;线条流畅柔顺,点触皴擦不露痕迹。作品的总体风格分为两类:一类源出于藏族居住区东部噶玛嘎孜画派,受到南宋及明代浙派、宫廷绘画青绿重彩的影响,有些作品创造性地将原本大片的青绿改为金黄色,人物形体吸收后藏拉孜县平措林寺壁画佛菩萨造像的特征,画面构图疏朗,上师、罗汉或大成就者题材采用不对称构图,在传统用线技法基础上,更加侧重晕染皴擦技法;另一类是传统单色唐卡如黑唐、红唐的改进样式,艺术家对泥金的运用出神入化,在单色勾线中略加几种相近色彩的傍线淡染,从而形成单色平面唐卡的二维与多维效果,使得原本沉寂平面的黑、红单色唐卡形成了一种纵深感。这是近年藏族居住区唐卡艺术最有益的探索之一,也是善于创造的觉囊绘画以时轮金刚黑唐为代表的绘画技法发展的结果。
北宋画家王希孟年仅18岁就创作出了令世人震惊的长达十余米的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有人质疑画师这么年轻如何能创作出如此宏大而精细的画卷,看到本卷觉囊唐卡传习所学员的画作,我们可以相信宋徽宗的画院确实培养出了王希孟这样才华出众的艺术家,青绿重彩山水的绘画与唐卡的绘画有相通之处。包括觉囊唐卡传习所在内的藏族居住区各地的唐卡画院,能在倡导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数十年间培养出一批技艺精湛的年轻艺术家,不只是得益于各位敬业的优秀教师对学员悉心传授技法以及学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激励,也不仅限于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支持,更是我们这一批年轻艺术家不为市井的喧嚣繁华所困扰,甘于寂寞,以执着、笃定的精神致力于艺术创作与研究的成果。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一名优秀的唐卡画师,确实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这些年轻艺术家用虔诚的心来绘画,近乎苛刻地使用饱含活力的线条,用微细的笔尖点阵渲染出渐变的天空,用如丝的细笔描摹毛发与织物图案的细节;较大尺幅、重在刻画细节的唐卡,需要绘制数月甚至经年,更要时时注意画面整体的协调与统一,画面的繁简疏密、色彩的冷暖与形体的凸凹,线条的前后一致,这些都需要在整个绘画过程中保持稳定良好的心态,任何情绪的波动都会在画面中留下痕迹。正如觉囊唐卡传习所创办者壤塘藏哇寺嘉阳乐住上师所说,绘画唐卡如同笔端修习,是一个磨炼、调整、把握自己心性的过程,也可以说绘画唐卡就是一种修习的实践,心绪的散乱会在作品中留下痕迹。这也就是藏族唐卡的杰作为什么大多出自高僧大德和大成就者之手,而藏传佛教史上的大学者同时也是大艺术家的原因。
《觉囊卷》以文字和图像记录了明中叶以来从卫藏腹地辗转至东部康区,一个具有悠久传承史并能在新的时代不断调适、改变,进而发展壮大的藏族艺术案例,也是《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系列的一个缩影。